詩不可說丨我有所念人,隔在遠遠鄉,白居易對湘靈的情深愛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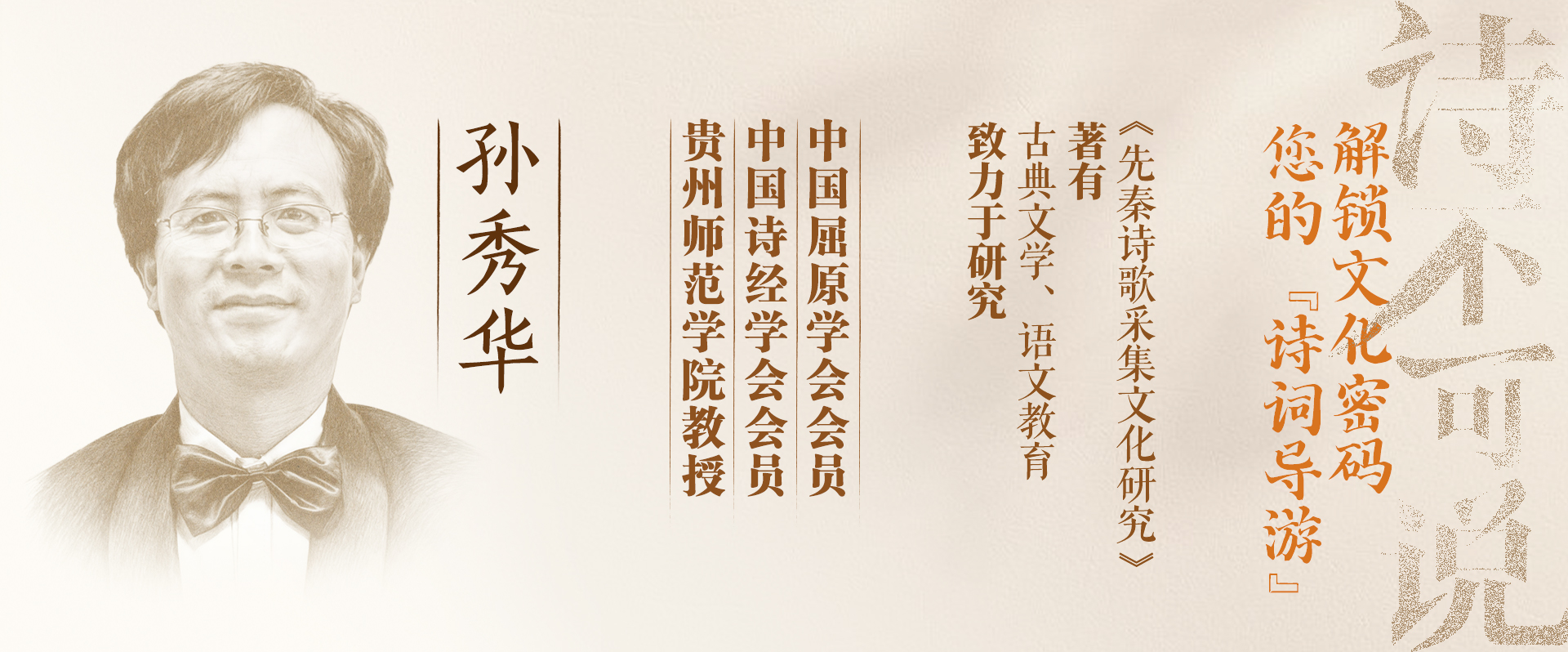
白居易《夜雨》詩曰:
我有所念人,隔在遠遠鄉。
我有所感事,結在深深腸。
鄉遠去不得,無日不瞻望。
腸深解不得,無夕不思量。
況此殘燈夜,獨宿在空堂。
秋天殊未曉,風雨正蒼蒼。
不學頭陀法,前心安可忘。
秋夜沉沉,風雨蒼蒼,所念人,所感事,百千縈繞,癡情思念在回憶的沉淀中變得更加味道醇厚,濃到化不開。該詩以最樸素的語言,直抵情感的核心。“遠遠鄉”與“深深腸”形成了尖銳的不可調和的對立,“無日不瞻望”與“無夕不思量”的時間延續則是全天候不間斷的綿綿思念。尤為深刻警覺的是最后兩句,“不學頭陀法,前心安可忘。”白居易于此坦言,自己無法像修行的頭陀那樣忘卻前塵,因為那個人、那些事、那些記憶已經構成了自我的一部分。這樣的詩句與當今流傳甚廣的“世間安得雙全法,不負如來不負卿”一語情韻相通,各彰其妙。
這是寫于元和六年(公元811年)一個秋雨夜晚的詩篇,白居易時年四十歲。到底是誰讓已至不惑之年的白居易如此心心念念而形諸詩章呢?那便是遠在家鄉的風姿綽約的白居易的鄰家女子湘靈。

唐德宗建中三年(公元782年),為避中原戰亂,十一歲的白居易跟隨家人遷居徐州符離(今安徽宿州),這個位于汴河與濉河交匯處的美麗小城,見證了他與鄰家女孩湘靈人生初遇的美好。白居易的《鄰女》詩寫于他十九歲的時候,白居易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自然流露出來。白居易《鄰女》詩云:
娉婷十五勝天仙,白日姮娥旱地蓮。
何處閑教鸚鵡語,碧紗窗下繡床前。

寥寥數語,詩歌便活靈活現勾勒出一個靈動美好的少女形象。值得注意的是,白居易將湘靈比作“白日姮娥旱地蓮”——白天的嫦娥與旱地的蓮花,這兩個意象既贊美了湘靈天仙般的美麗,也暗示了她對于白居易而言的特殊性。通常而言,贊美嫦娥都是因夜月而引發,都是在夜晚的場景,心悅蓮花的清新美好也往往都指向水中蓮花。白居易于此詩句中反其道而行之,自然是獨有的“愛的感覺”,即便贊美鄰女為天仙,那也是與眾不同的天仙。這世上那么多人,何止千千萬萬,但我的眼里唯有你是天仙,是特異的唯一的無與倫比的天仙。白居易如此的愛意綿綿,簡直不要太甜!
白居易《晝臥》詩曰:
抱枕無言語,空房獨悄然。
誰知盡日臥,非病亦非眠。
這樣的情景與情愫,應該就是白居易的“愛的初體驗”了。顯而易見,此等詩作,大約正是白居易在傾訴愛情的寂寞與等待,可能也是患了一種病吧,那就是“相思病”。

愛情如此美好,但現實卻如此殘酷。貞元十年(公元794年),為了家族期望和個人抱負,二十三歲的白居易離開符離,前往父親任職的襄陽,開始了漫長的求仕與為官之路。或即在赴襄陽途中,白居易寫下了《寄湘靈》:
淚眼凌寒凍不流,每經高處即回頭。
遙知別后西樓上,應憑欄干獨自愁。
我念所念之人念我,我愁所愁之人“自愁”。前兩句中,“凍不流”三字極具創造性——淚水在嚴寒中幾乎凍結,這一意象既表現了天氣的寒冷,更暗示了內心痛苦的凝固狀態。而后兩句運用了“對寫法”,不直接寫自己的思念,而是想象對方也在思念自己,這種雙向的情感投射,創造了更為豐富的詩意空間,把情愛主題表達得更為充分。
白居易還另有一首《冬至夜懷湘靈》,話語親切明白,卻最為深情。白居易《冬至夜懷湘靈》詩云:
艷質無由見,寒衾不可親。
何堪最長夜,俱作獨眠人。
白居易創作有《潛別離》與《生別離》兩首專寫別離的“雜曲歌辭”,都較為沉痛,或也與他愛情的經歷相關。如白居易《潛別離》歌曰:
不得哭,潛別離。
不得語,暗相思。
兩心之外無人知。
深籠夜鎖獨棲鳥,利劍春斷連理枝。
河水雖濁有清日,烏頭雖黑有白時。
惟有潛離與暗別,彼此甘心無后期。
后十余年,元和元年(公元806年),白居易與友人陳鴻、王質夫同游仙游寺,談及唐玄宗與楊貴妃的往事。在友人的建議下,他創作了千古傳誦的《長恨歌》。這首長達120句的敘事詩,通常被解讀為對帝王愛情悲劇的描寫,但其中自然而然又深深烙印著白居易個人的情感體驗。
細讀《長恨歌》,不難發現其中多處與白居易思念湘靈的詩歌形成互文關系。例如名句“在天愿作比翼鳥,在地愿為連理枝”,這與白居易早年思念湘靈時所作《長相思》中的“愿作遠方獸,步步比肩行。愿作深山木,枝枝連理生”何其相似!這種意象的延續性,暗示了《長恨歌》中流淌的不僅是歷史人物的悲歡,更是詩人自身的情感投射。
更深一層的理解便是,白居易《長恨歌》通過將個人情感投射到歷史題材中,實現了私人經驗的歷史化升華。詩人將自己對湘靈的思念、對愛情阻隔的痛苦、對永恒分離的遺憾,都融入了李楊愛情悲劇的敘述中。這種創作策略將個人情感體驗提升到家國敘事的高度,又普適了真摯情切的人性的廣度,這或許才真正是白居易《長恨歌》獲得讀者廣泛共鳴的奧秘所在。

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,四十四歲的白居易因上書言事觸怒權貴,被貶為江州司馬。這次貶謫成為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,也意外地促成了他與湘靈的重逢。在赴江州途中,經過符離,白居易意外遇見了湘靈。此時兩人已分別二十余年,當年的翩翩少年與如花紅顏,都已青春不再。這次重逢的場景,在白居易《逢舊》詩中被記錄下來:
我梳白發添新恨,君掃青蛾減舊容。
應被傍人怪惆悵,少年離別老相逢。

蛾眉,專指女子的眉毛。因此,白居易此詩所寫的重逢舊人,是他心心念念的湘靈無疑。這首詩在藝術上采用了精煉無比的對比手法,“我”對“君”,“梳”對“掃”,“白發”對“青蛾”,“添”對“減”,“新恨”對“舊容”;“少年離別”對“老相逢”。這些精準對比不僅展示了歲月的無情流逝,更凸顯了情感在時間中的堅韌存在。
在江州司馬任上,某個晴好的日子,白居易“中庭曬服玩”,忽然發現了湘靈早年贈予他的一雙錦鞋,鞋上繡著“永愿如履綦,雙行復雙止”的愛的誓言。睹物思人,情感噴薄而發,“為感長情人”湘靈,白居易寫下了一首題為《感情》的詩作。白居易《感情》詩曰:
中庭曬服玩,忽見故鄉履。
昔贈我者誰,東鄰嬋娟子。
因思贈時語,特用結終始。
永愿如履綦,雙行復雙止。
自吾謫江郡,漂蕩三千里。
為感長情人,提攜同到此。
今朝一惆悵,反覆看未已。
人只履猶雙,何曾得相似。
“人只履猶雙”,物是人非,人是孤單人,鞋子卻“成雙”,讓人情何以堪。這首詩通過凝結情愛的“故鄉履”,串聯起了從過去到現在的時間跨度,從符離到江州的空間距離。“雙行復雙止”的誓言與現實中“人只履猶雙”的對比,道盡了命運的無常與情感的執著。
唐文宗開成五年(公元840年),六十九歲的白居易寫下最后一首關于初戀湘靈的詩歌《夢舊》。白居易的詩歌大都是經過他本人親自編定的,他的“舊人”朋友有很多,但白居易《逢舊》詩寫給了湘靈,那么這首《夢舊》自當便指向了白居易魂牽夢繞的湘靈。白居易《夢舊》詩云:
別來老大苦修道,煉得離心成死灰。
平生憶念消磨盡,昨夜因何入夢來?
很久沒有入夢來了,這次夢到湘靈的情景如何,可能第二天寫詩的時候,白居易自己也記不得了。因此,才有那癡癡追問夢中人的念頭,“昨夜因何入夢來”?盡管試圖通過“修道”來消解思念,將心煉成“死灰”,但夢境卻背叛了意識的控制,讓早已消磨的記憶重新浮現。這種意識與潛意識、理性與情感的沖突,展示了人類心理的復雜層次,在“科學層面”上,揭示了情感記憶的不可控性;在文學表達上,寫盡了思念成災,終生不忘,刻骨銘心。
會昌六年(公元846年),七十五歲的白居易在洛陽逝世。據傳,他臨終前要求家人將其部分詩稿與湘靈早年贈予的信物等一同陪葬。
“我有所念人,隔在遠遠鄉。
我有所感事,結在深深腸。”


